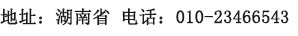导演手记
文|张艳芬
你知道太湖有多少种颜色吗?
太湖,对于从小在北方长大的我来说,长久以来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地理教科书的刻板描述:中国第三大淡水湖、横跨江浙两省、特产太湖三白……尽管已经在太湖流域的上海生活了十几年,却一直无缘一睹太湖的真容。直到年1月,开始拍摄纪录片《太湖之恋》,才有了长达两年的与太湖的亲密接触,并且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太湖人。
摄制组在太湖无人岛拍摄
初遇太湖
年1月16号-18号,临近春节,《太湖之恋》第一次带机看景,地点选在了因太湖而得名的湖州市。汽车沿着滨湖大道缓缓前行,太湖随之呈现在我的眼前。冬天的太湖,白茫茫的一片,水雾氤氲中难见全貌。这是太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后来多次到太湖边拍摄,她总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,隐藏在雾气中,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烟雨江南吧。
这次看景,我们见识了古老东方智慧的魅力:多年前的古老水利工程溇港,以及由它发展而来的桑基鱼塘系统;看到了南太湖新区渔民上岸后,湖水清澈,月亮酒店矗立的新模样;走访了退蟹还湖后,开启全新养殖方式的蟹农龚叔的大闸蟹基地;走进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源地余村。
而我们也带着深深的思考,这块凝结着古代智慧的神奇土地,为什么又同时成为了新时代“生态文明”的诞生地呢?
摄制组在湖州荻港村
勘景“桑基鱼塘”系统
摄制组
在安吉余村勘景
摄制组在南太湖新区勘景
看景之旅收获满满,我们都摩拳擦掌准备着春节拍下一个热热闹闹的太湖。谁料,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。真正开始拍摄已经是2个多月之后的事了。
美就美在太湖水
无论如何,年的春天还是如约而至。3月下旬,我们的拍摄工作正式启动。拍摄的第一站仍是湖州。
清晨5点不到,我和摄制组的小伙伴们已经悄悄来到南太湖沿岸,我们要陪着太湖一起苏醒。穿过月亮酒店蜿蜒的小路,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水天一色的绝美风景。没有水汽的阻隔,今天的太湖澄澈而清晰。我们不禁连连惊呼,太湖真的太美了。渐渐地,水天相接的地方开始泛起红晕,像小灯泡一般的太阳慢慢从地平线升起,橘黄取代浅蓝,成了太湖的主色调,太阳和它水中的倒影,组成了一个倒着的感叹号!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《太湖美》里的那句歌词:“太湖美,太湖美,美就美在太湖水。”
摄制组在太湖边拍摄日出
太湖日出
晨曦和夕阳,是一天中光线最美的时刻。为了最大程度拍出太湖的美,摄制组不得不一次次披星戴月。能够发现并记录下普通人见不到的绝美,这就是纪录片人的责任和幸运吧。
太湖美景
被淹的莼菜基地
在太湖拍摄的过程中,常常有惊喜,不时也有意外。年6月,洪水造访江南,我们的拍摄工作不得不短暂搁置。等到洪水退去,我们原本拍摄过的莼菜基地竟然被水淹了。
莼菜
莼菜,太湖水八仙之一,是太湖水赐给江南人的宝贵水产资源。太湖莼菜被誉为“水中碧螺春”,可见其娇贵特性。近年来,由于种植面积逐渐萎缩濒临灭绝。保持着原生态环境的苏州东山,是太湖莼菜赖以生存的一块净土。我们的主人公叶玉泉就是苏州东山莼菜基地的负责人。80后的他日本留学回国后,从父亲手里接过家里的莼菜基地,做起了农业。
叶玉泉与父亲叶洪兴在莼菜基地
叶玉泉的莼菜基地在靠近太湖的一片水域里。坐车穿过一段颠簸的乡村道路,还要乘船5分钟,才能抵达。我们到东山的第一天,莼菜基地水位虽然较平时有所上升,但影响不大。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叶玉泉和父亲在莼菜基地的影像。谁曾想,这竟是这个基地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段影像。
摄制组拍摄采莼菜
叶玉泉的莼菜基地
按照约定,第二天一大早,五点钟左右,我们跟着采莼菜的阿姨们一起出发,记录她们采莼菜的过程。抵达莼菜基地后,迎接我们的却是一片汪洋。原来,昨晚太湖水位上涨,倒灌进莼菜基地,叶玉泉几年的心血,就这样没了。
说到这里,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叶玉泉。为了我们的拍摄顺利进行,他交代好自家基地的处理事宜后,又亲自开船,带我们去到一小时路程的另一个莼菜基地,在这里,我们零距离记录下了采莼菜的艰辛。一个小小的菱桶,阿姨们一趴就是七八个小时,一天下来,腰都直不起来,手也泡的发白了。由于采莼菜太过辛苦,年轻人都不愿意干,只有老一辈的人还在坚持。我们拍摄的李莲珍阿姨忍不住感慨:再过几年就吃不到莼菜了,我们都老了,年轻人都不愿意采。这也是莼菜产业面临的问题。年轻的叶玉泉在思索莼菜未来的发展方向。他告诉我们,他正在研究以机器采摘代替人工的可能性,我们都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。
采莼娘李莲珍
拍摄结束后,我和叶玉泉也一直保持联系。令人略感欣慰的是,他的新莼菜基地已经建了起来。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记录,为他消失了的老基地留下珍贵的记忆。
与喝茶有关的故事
凌晨4点起床,除了拍日出,还能拍茶馆。隐藏在江南水乡的茶馆们,早上4点左右就开门营业,他们不为赚钱,为的是给早起的爷叔们一个休闲聊天的地方,这也是独属于江南的生活方式。
摄制组拍摄湖州荻港村茶馆
拍摄太湖的过程中,我一共拍了两个凌晨4点钟的茶馆。一个在湖州的荻港村,一个在上海的朱家角古镇。这两个茶馆都有着悠久的历史,荻港村的“一元茶馆”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,破旧长条桌椅写满岁月的痕迹,附近的村民只要花上一块钱,就能坐上半天;朱家角的“江南第一茶楼”则被装修一新,白天正常营业,清晨的几个小时免费开放给附近的居民,爷叔们自带茶叶而来,店里还提供免费的开水。
朱家角“江南第一茶楼”
江南人喝茶可以很随意,随意到一小撮散茶、一个玻璃杯就可以喝上半天;江南人喝茶也可以很讲究,讲究到茶器都必须用上品紫砂。
江南之滨的小城宜兴,不折不扣的紫砂之都。这里拥有余年的制陶史和一代代能工巧匠。直至今日,宜兴仍户户捣泥、家家制壶。在这里,我们拍摄了创烧于明代的前墅龙窑;记录了紫砂矿变成紫砂泥,再变成紫砂壶的全过程;结识了紫砂泰斗李昌鸿,虽然已经85岁高龄,依旧精神矍铄、声如洪钟。我们的故事里有老一辈紫砂人的坚守,也有年轻一代的创新。
摄制组拍摄
采紫砂矿情景再现
李昌鸿教孙女
李千蕙做紫砂壶
摄制组与紫砂大师李昌鸿一家合影
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?
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中写道:“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?”印象中的园林里总是游人如织,因此一直get不到江南园林之美。这次为了拍摄《太湖之恋》,我们得以赶在普通游客之前进入,才真实感受到了私家园林之美。狮子林里回环往复的假山群、拙政园“四壁荷花三面柳”、留园“冠云峰”、豫园“玉玲珑”,清逸秀丽、移步换景。空无一人的园子里,恍惚间产生了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的错觉。从早上5点进园等天亮,到7点普通游客入园,在这短暂而奢侈的一个多小时里,我们用摄像机镜头争分夺秒地记录下这些最美的江南画面。
江南园林
昆曲是流动的园林,园林是凝固的昆曲。当传统的江南园林遇上传统的昆曲,碰撞出新的火花。采访昆曲演员张军,是在朱家角古镇的课植园里。这里是他主创的中国首部实景园林昆曲《牡丹亭》的演出地。多年来,张军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发展昆曲这门传统艺术,直到他遇见了古典园林课植园,一种全新的结合出现了。张军至今记得《牡丹亭》在世博会首演后,纽约时报做了两个整版的报道,题目叫做《中国花园里的莎士比亚》。
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军
我们用镜头记录下这场既传统又现代的昆曲演出,并把它作为第一集故事的结尾。或许这就是江南,千百年来一直在改变,似乎又从未曾改变。
实景园林昆曲《牡丹亭》剧照
拍摄太湖的故事还有很多,比如拍摄蚕宝宝拍到自己带回家养了起来、架着机器拍吐丝;在桑基鱼塘的狭窄小道上、借了村民的小三轮拉着设备狂奔赶日落;在太湖中的无人小岛上演“荒野求生”……点点滴滴,辛苦和快乐并存,而太湖对我来说,早已不再是一个名词,而是一份深深的眷恋。
开三轮
而我在初识太湖时的疑问,经过两年的时间,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。这块凝结着古代智慧的神奇土地,有的远不止辉煌的历史。而且我拍摄的这么多“世界遗产”、“世界灌溉工程遗产”、“国家非遗”,讲的也不仅仅是历史,而是一代代太湖人活泼泼的生命力。是他们让太湖永远年轻,让“遗产”依然鲜活,让太湖有了这么多色彩。
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
刘丽婷工作室出品
纪录片《太湖之恋》
1月4日起每周二晚22点
东方卫视播出
百视TV全网独播
▼
原标题:《纪录片《太湖之恋》|你知道太湖有多少种颜色吗?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