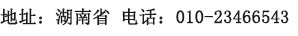明代士大夫对演剧醉心的程度,似乎只有魏晋文人对药与酒的沉溺,始能相拟。徐复祚《曲论》记载衡州太守冯冠,“少善弹琵琶歌金元曲,五上公车,未尝挟,惟挟《琵琶记》而已”。可以说他对戏剧的爱好超过了对功名的热衷,但更典型的事例是《昙花记》的作者屠隆的丢官。屠隆是万历年间的名士,官至仪制郎中,不仅擅长编制传奇,同时也长于打鼓和串演,据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载录,屠隆颇以扮演自炫,“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伎”,某次作场时适逢“有才色,工音律”的西宁侯(宋世恩)夫人在座,“夫人从帘箔见之,或劳以香茗”。这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,然而却被刑部主事俞显卿诬劾谓与西宁侯夫人有私,终于在甲申岁(万历十二年)罢职为民。
此后更加寄情声色,置家乐教演《昙花记》等剧,指挥如意,三十一年更在乌石大会诸部梨园汇演的场合,幅巾白衲,奋袖作《渔阳掺》。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,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官场的燕集、名士的交游,无不借演剧助兴。明代初年,士大夫的好尚还只限于北曲杂剧;自《琵琶》《拜月》风行,名人才子,竞作传奇。特别是嘉靖、隆庆间出现了魏良辅、梁辰鱼等笃志改革的戏曲家,使原来还比较质朴的昆山腔演变为流丽悠远的新声之后,士大夫们便借创作和演出以炫弄自己的才华,同时也用之娱目怡情。
虽然道学家们屡屡责难,并敦促个别的皇帝向臣下们提出了婉曲的批评,然而要把演剧从士大夫的生活中排除出去,那是谈何容易的事!既然连宫廷中也不曾杜绝演剧的娱乐,士大夫又何妨在这方面发展自己的兴趣?只是不必到教坊寻欢作乐、招摇过市就行了。在士大夫的行列中,对演剧产生兴趣的出发点是不尽相同的。总体说来,大多出于享乐的要求。杨慎《丹铅总录卷十四和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卷九证实,士大夫们在嘉靖与万历两个不同阶段中,先后对海盐腔和昆山腔下过一番钻研的功夫。在少数士大夫中,这种钻研出于对艺术的热忱。
《红拂记》的作者张凤翼就属这一类型的人,据称他居家不仕,“自晨至夕,口呜呜不已”又尝与其子合串《琵琶记》,“父为仲郎,子赵氏,观者填门,夷然不屑意也”(徐复祚《花当阁丛谈》卷四十三)。有些人二者兼具。以张岱为例,情况就比较复杂,说他是艺术气质使然吧,他又放荡而多玩世不恭之行。在自撰的墓志铭中,他毫不隐讳地供认自己“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”(见《琅嬛文集》卷五)如果单从这段文字来看,张岱也不过是地主阶级中的浪荡子弟,他对戏剧的喜爱,也不过像对骏马、饮食、烟火、色情的沉溺,以之充当生活的点缀和享受而已。
《陶庵梦忆金山夜戏》另一次,他和兄弟在天启三年()“携南院王岑、老串杨四、徐孟雅、园社河南张大来辈”往观陶堰严助庙的庙会,恰值村民从越中聘得梨园搬演戏剧,张岱即指令王岑扮李三娘,杨四扮火工窦老,徐孟雅扮洪一嫂,家乐马小乡(十二岁)扮咬脐郎,串《白兔记》中《磨房》《撇池》《送子》《出猎》四出,蓄意压倒梨园,造成“戏场气夺,锣不得响,灯不得亮”的局面。和张岱交往密切的一些人如祁止祥、张噩仍等,大多具有同样的气质。《琅嬛文集公祭张亦语文》谓亦寓“拨阮弹笋,以昼卜夜,被放归里,时时凝碧,日日梨园,演剧征歌,缠头撒漫”。
《公祭张噩仍文》谓噩仍“精于音律…见有梨园子弟歌喉清隽,必鉴赏精详,盘旋不去,如公瑾之按拍审音,而半字差讹,必得周郎工一顾”。可见,在晚明阶段,像张岱这样生活上很放纵、对演剧却又极具热情的士大夫为数并不少。如果我们感到这类人比较难下判断的话,那么,和张岱同时的祁彪佳,总称得上正统典型的士大夫吧。这个人在南明弘光朝以右都御史巡抚江南,致力恢复,颇得将士爱戴,却由于马士英之党的嫉妒排挤,未几告归。清兵破南京下杭州后,曾遣使劝他出降,他以自沉殉国回答。他的民族气节既为人们所钦重,对生活的态度一向也很严肃,处世立身多以封建道德自励。但就像他这样的士大夫,对观赏演剧竟也有浓厚的兴趣。
他搜集了八百多部元明戏剧作品,自己也撰写过《全节记》和一些散曲,他的戏曲论著《远山堂明曲品》《远山堂剧品》不仅著录元明七百种剧作的名称和作者,还作了虽则简略却很严肃的评价,其中甚至包括一般文人所看不起的民间艺人的剧作。他的日记录载了大量观看演剧的活动,提供了晚明浙东地区流行戏剧的可信资料。不难看出:这个人在他有限的一生中,对戏剧的研究和演出投掷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!而且,通过他的日记,我们看到了与他往来密切的朱佩南、林自名、吴俭育、祁止祥、钱德舆、蒋安然等一批士大夫之间的交往活动,无不以观赏演剧为中心,
十八日:赴阮旭青、凌若柯席,观拜月剧。二十日:邀冯弓闾、徐悌之、施季如、潘葵初、姜端公、陆生甫观半班杂剧。公安派“三袁”之一的袁小修《游居柿录》也有类此的记载:诸公共至徐寓演《明珠》,久不闻吴歈矣,今日复入耳中,温润恬和,能去人之躁竞。…廿九日……晚赴李开府约于魏戚畹园,封公在焉。招名优演《珊瑚记》。米友石见召,同君御、修龄诸公,命歌儿演新曲城西净业寺前。同龙君御、米友石饭于长春寺,寺在顺城门外,斜阶看演《昙花记》。十五日雨甚,李开府名植召饮,灯火甚盛,出歌儿演新曲。封公教有歌儿一部,演吴曲颇倩越。
《琅嬛文集-》 谓祁文载“留心字艺,游戏词坛,教习梨园,有老优师所不经见者”。袁宗道指出:(《白苏斋类集》卷十六“笺牍类”)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,辞官归里后成了千余艺人的顾问,他和艺人罗章二的通信中就曾针对《牡丹亭》的演唱作过指点:
上面列举的这些材料,都属于原则性的、比较抽象的,更典型而具体的,可以举冯梦龙。他在《墨憨斋定本传奇》中,处处考虑如何有助于艺人的演出,从角色扮演到唱腔、服装、道具于关键处都极为细致地提出指点:例如在卖国贼秦桧杀害民族英雄岳飞为题材的传奇《精忠旗》里,他就扮演情节、动作、表情,都按剧中人物的思想性格、社会地位与特定环境作了简要的分析:
家乐的备置,原是汉唐的遗风,历来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士大夫,总是自备一套家乐的,以白居易来说,所谓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”,名虽侍姬,实质上不过是高级的家乐,白太傅晚年又买谢好好商玲珑教习《霓裳羽衣舞》曲,都是明证,只不过那时由于戏剧尚处于过渡阶段,家乐的内容每限于乐器与歌舞罢了。从表演戏剧的家乐来说,元时代已经有了。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记张浚之孙张镃在海盐“作园亭自恣,令歌儿衍曲,务为新声,所谓海盐腔也”。海盐腔的创制是否发端于此,这是另外一个问题,但从这则记述来看,张镃备置家乐还是可信的。
明代爱好戏剧的士大夫们,沿袭了风习,特别是在政治上处于不甚得意的情况下,或因年老致仕,往往把时间精力寄托在备置和训练家乐方面。王九思和康海因依附刘瑾而被罢归之后,不惜“费重资购乐”,“挟声伎酣饮”,汤显祖解组还乡,就“自掐檀痕教小伶”,无锡邹迪光罢官之后“征歌度曲,筑惠锡之下,极园亭歌舞之胜“。阮大铖为人,品格虽然卑下,但从戏剧表演与创作来说,却是公认的行家。我们还应该看到,张岱对戏剧既爱好也素有研究,他家从父辈起就先后备置和培养过“可餐”、“武陵”、“梯仙”、“吴郡”、“苏小小”、“茂苑”六个家乐班子。
张氏声伎,名满东南,其中造就了不少杰出的演员,而受张家培训指导的伶人把在他家学艺的过程比之为“过剑门”,其眼界与造诣之高可想而知。连他都对阮大铖的家乐如此钦重,足见阮氏家乐确有水平。事实上,这种水平是经过一番苦心培植的。胡介社在《壮悔堂集》卷首《侯朝宗公子传》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:初,司徒公(侯朝宗之父侯恂)亦留意于此,蓄家乐,务使穷态极工,致令小童随侍入朝班,审谛诸大老贤忠佞之状,一切效之排场,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。至是投老寂寞,公子乃教成诸童,挈供堂上次,司徒公为色喜。而里中乐部,因推侯氏为第一也。
看来高水平的家乐,除声律的钻研而外,甚至带有体验生活的因素在内了。李开先在王九思家听出了《游春记》(作)赏花时曲“四海歌万姓欢,谁家数去酒杯宽”注脚走入“桓欢”韵的错误,就应王之请即席代为改正(事见李开先《词谑》),对剧作者、对演员与演出都有提高的作用。而且,由于家乐班中傒僮小鬟走向广阔的社会(参见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所记曾见老乐工数人谙弦索,皆何元朗家乐流散之余。又见袁小修《游居柿录》亲睹乃兄之旧伶事),也就必然要在民间舞台的扮演中,散播他们曾经受过的严格训练的影响,从而使民间戏剧的演出从组织调度到唱做技术都有所获益。
吴伟业《过东山朱氏画楼有感》诗序,谈到太湖东洞庭碧山里朱君,“筑楼教其家姬歌舞……楼有赤阑累丈余,诸姬十二人艳妆凝眸,指点归舟于烟波霭间,既至即洞箫钿鼓,谐笑并作”正和“庚辰以来,遂兴土木,造船楼一二,教习小傒,鼓吹剧戏”的张岱亦复类似。培训一堂家乐,除在吴地购买傒童小鬟之外,还要添置全套乐器,延聘高手名工传授、制备各式行头、建构舞台、配备场面…这一切,都要耗费大量钱财;经常的排练、演出,也不是轻易措办即可应付的,倘非豪门巨室,绝对供养不起。
沈周《戏儿棚》诗所谓“脂粉两般迷眼药,笙歌一派败家声”之句,是可以转引为家乐挥霍的写照的。张大复《梅花草堂集》叙谭公亮“故有家法,诸伶歌舞达旦,退则整衣肃立,无昏倚之容”,这种要求是多么苛刻啊!我们必须领会家乐的演员们在强颜欢笑下掩盖的悲楚,并且从家乐在舞台上昙花一现的魔术式的“荣华”中,看到艺术对那个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无情讽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