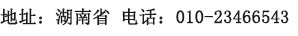本篇内容为虚构故事,如有雷同实属巧合。
1
月色清凉如水,悬在天心处的玉盘在院子里泻下一地清辉,覆了满院银霜。
我已经等了许久,等到更深雾重,等到衣裙早被露水沾湿,我仍不肯起身,固执地坐在台阶上等。
流心想搀扶我起来,还说:“小主,夜色都这么晚了,陛下一定不会来了。”
但我不信,我相信他一定会来,这后宫只有我最懂他,没人比我更明白他心底在想什么。
果真,他踏着月色而来,走路颤颤巍巍,一身酒气,酩酊大醉。
饶是如此,依旧掩藏不了他眉宇间气吞山河的不凡气概,和浑身散发着凛然孤傲的高贵之气。
我如痴如醉地望着这张脸,也只有这时候,我才能离他最近,近得好像只有我能独占。
“陛下来了。”我笑着行礼,然后想过去搀扶他,却被他拂袖甩过。
我一时僵在那,面色十分难看,可也只是一瞬,毕竟他来了不是吗,我还能奢望其他什么呢。
看到我备好的糕点,他十分满意地道:“定舒,朕就知道在整个宫中,只有你最明白朕,也只有你能听懂朕的倾诉。”
时隔多年,这是他第一次唤我名字,仿佛眼前又回到儿时岁月。
可是我明白,他唤的虽是我,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,那个他这么多年都不肯放下的人。
他拿了块杏仁佛手送入口中,似乎陷入回忆里,眉眼里皆是温情:“这是她最爱吃的点心,吃了多少年都不觉得腻,你说她怎么这么固执?”
我笑着倒了杯茶:“朝阳郡主一向如此,喜欢什么就会一直喜欢,她总说,不论什么能被人喜欢着都是幸福的,所以她会经常喜欢上各种东西。”
我叙叙说着,他便在旁边认真地听,仿佛像个孩子般,央求着大人讲故事。
他喜欢听我说起朝阳,无论他已经听过多少遍,他还是会听,年复一年,从不厌倦。
只因讲的是朝阳,而他最爱的便是朝阳。
朝阳是太后贴身婢女的女儿,她娘生她时死于难产,后被太后接入宫中并收为义女,封为郡主。她和皇上从小认识,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若非她溺水湖中,这后宫又哪会有别人的位置。
我从小跟在他们身边,最能体会他们之间的感情。
也只有我最明白,自朝阳死后,皇上那颗温热跳动的心自此冰冻,再不会对谁动心。
在他心中,朝阳这世间只有一个,谁都替代不了。
比如丽妃,她容貌和朝阳看起来有七分相像。
又比如和妃,她孤身一人远离故土,就像朝阳在宫中无亲无故,什么都要靠她自己。
再比如玉贵嫔,她娇媚可爱,想法千奇百怪,像极了从前的朝阳,脑中总能有鬼灵精怪的主意,让人止不住好奇,然后沉迷其中。
他看似喜欢宠爱她们,却只不过是喜欢她们其中一点,然后拼凑起来,变成他心底的朝阳。
后宫知晓朝阳存在的不多,就算知晓也不放在心上,毕竟一个死人,又如何能和活人争宠呢。
她们太天真,自以为可以牢牢抓住皇上的心,殊不知她们自始至终,根本从未看透过这个少年天子。
否则,她们就会如我一样,看到他眸子里深藏的落寞和悲恸,更会看见他作为一个帝王失去挚爱的绝望与痛苦。
就像他眼中从没看到过我,却仍在每年朝阳生辰这天,来到我的寝宫,听我讲朝阳的旧事。
我还在讲着,可他醉得快倒下了,正当我犹豫是否去扶他时,他已站起来,再不看我一眼,踉跄着走出去。
他一向这样,我在他心中什么都不是,也从不让我碰触。他封我为婕妤,也不过是念在我和朝阳情同姐妹的情分上。
我于他而言,永远只是眼中看不见的一粒尘埃。
2
但我怎么都想不到立后这等天大好事,最终会落到我头上。
皇上登基多年,后宫嫔妃不少,却迟迟不曾立下中宫,只因在他心中,皇后之位只能属于朝阳。
是以他能拖就拖,理由借口用了一大堆,直到真的搪塞不过去时,他终是答应考虑立后。
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在德妃和丽妃中选择时,他竟不顾一切推举出我,当众宣布会立我为后。
这话一出,无数朝臣纷纷上书,非说凭我一个太医之女,如何能担中宫之位。
可他根本不予理会,力排众议,还当场扬言:“朕已经决定了,此事莫要再提,朕一概不听!”
我听到消息时,几乎以为听岔了,我深知他痴爱朝阳,却不知他竟能做到爱屋及乌的地步。
这是多少人渴望的皇后之位,竟是让我一个最毫不起眼的婕妤得到。
我既激动又欢喜,那一刻,我最能想到的是,不管他爱的是谁,眼下他心中至少还是有我的。
后来一个月,我都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,好似一切都虚幻得太不真实。
尤其是无数妃嫔来对我恭祝贺喜时,我几乎以为这是场梦。
我在后宫一直默默无闻,又向来懦弱胆小,从没人意识到我的存在,几乎当我透明。
这是头一次,她们知晓认可我,也是头一次,她们以我为中心,眼中皆是对我的艳羡和嫉妒。
我好怕这只是梦,一旦梦醒了,什么都会恢复到原位。
直到封后大典仪式结束,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,这不是梦,这真的就是我。
满皇宫的树枝上都系着朱红色绸带,鲜艳如血的红色地毯一路从皇宫绵延至京城外,浩浩荡荡,尽显十里红妆,普天同贺。
我望着铜镜中的自己,云鬓高耸,头戴镂金点翠凤凰珠冠,穿一身正红色大朵金银丝线绣着的牡丹朝凤嫁衣,当真一番凤翥姿态。
脸上不觉浮现羞涩,待他过来,我该如何称呼,唤他夫君,还是陛下。
从此以后,我便是他的妻,他唯一的妻,不管如何,往后余生,我都要和他夫妻同心,风雨同舟,至死不渝。
这样想着,内心的激动更是不可言喻。
我便这么等着,天色逐渐昏暗,很快黑夜如墨,我望着红烛一点一点燃尽,却始终没等到他的到来。
我想催流心去问一问,但又觉着不该这般不知礼数,便又让流心回来。
也不知等了多久,等到我几乎快要睡过去时,外面终于传来魏公公的声音。我忙示意流心去开门,正欣喜地想去寻找那道身影,却发现并无别人。
魏公公进来微一欠身,然后道:“皇后娘娘,陛下让奴才过来传个话,今晚宴客太多,陛下暂时抽不开身,还望娘娘先行歇息。”
我莫名一阵失落,脸上却维持着适宜的笑容:“本宫知晓了,多谢魏公公。”
正等待他退出去,他却又说:“奴才还有一事,陛下还说,皇后娘娘虽手握凤印,但经验尚浅,遇事不明,现下不如让德妃娘娘暂代管理后宫,待以后再归还。”
凉意从心底漫出来,随着口中一阵腥甜,舌尖已被我咬出血来。
但我丝毫不让人察觉,而后笑着示意流心,将一沉甸甸的钱袋塞入他手中。
他退出门后,甫一关上门,流心就小声地道:“奴婢方才去打听了,陛下根本不在酒宴,而是宿在了玉贵嫔的棠梨宫。”
闻言,我再顾不上任何仪态端容,一把扯下头上的凤冠,重重摔碎在地。
我手紧紧捏着拳,指甲几乎要戳入肉里,却不觉得疼。因为心底某一处有什么在碎裂开来,痛得我喘不上气。
原来一切都是我的错觉,我以为他可能会有点在乎我,其实不过是帮他守着皇后的位置罢了。
他给了我皇后的身份,却夺走我关于皇后所有的体面和权力。
一抹凄凉悲怆的笑意从嘴角溢出来,我越笑越难以控制,最后眼泪流满了整张脸。
定舒啊定舒,到头来你终究还是,落得黄粱一梦的下场。
3
我成婚当天独守空房一事,于隔日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,尽管流心不肯告诉我细节,但我也能想象得到,她们定然都是面带讥讽,肆意嘲笑。
而我今早又不得不当众面对她们,尽管我只想逃,逃得越远越好。
晨昏定省是祖上定好的宫规,虽然我无皇后实权,但规矩还是要照做。
是以我早早就在凤仪宫等着,妃嫔们陆续来了,最后到的是玉贵嫔,她面色娇羞,柔媚无骨,朝我一福,语气娇嗔:“臣妾昨晚服侍陛下劳累,让皇后娘娘久等了,还请皇后娘娘责罚。”
她面色盈润,脸颊娇嫩,愈发衬得我脸色苍白,神情尴尬。这本应该是我的洞房夜,却变成了我的耻辱夜。
我强扯笑容:“后宫妃嫔自应以陛下为重,以子嗣为重,本宫又如何会怪你呢。”
德妃瞥她一眼,又看看我,柔柔笑道:“皇后娘娘当真是宽容大度,最识大体,众姐妹定要谨记皇后娘娘教导,一切以陛下和子嗣为重,为皇室开枝散叶才是最要紧的。”
闻言我身子微颤,心底冷得发寒。
德妃便是如此,她看似温柔娇弱,表面上弱柳扶风,实际上心思狠毒,手段凌厉。
她这话听着像赞我大度,其实不过是讽刺我,就算我当上皇后又如何,却连为皇上绵延子嗣都做不到。
是以妃嫔们虽站起身朝我跪拜,口中附和着她的话,但她们的神色无一不是讥讽暗笑,压根瞧不起我。
我望着德妃,她也看着我,她扬眉一挑,眸中的得意暗示着我的可悲和无能。
我知晓她恨我,她本是最有可能做皇后的,要不是我,她何苦还在妃位。所以我深知她会不顾一切羞辱我,折磨我。
可我向来能忍,从前还是婕妤时,谁都忽视我,谁都不搭理我,我仍好好地活着,现在虽换了身份,情形并无差别,我自然也能忍下去。
于是我扬唇笑道:“今日若没别的事,大家都散了吧!”
怎料德妃漫不经心地开口:“容禀皇后娘娘,臣妾还有一事。陛下让臣妾暂管后宫,自然事事都要悉心管理,切不能有半分差错和遗漏,更不能夹带私情,不知臣妾说的可对?”
我右眼皮莫名一跳,忽地生出不好的预兆,但还是点点头:“陛下相信德妃,自然是后宫一切但凭德妃做主。”
德妃笑了,盈盈起身,目光死死盯着我旁边的流心,语气威严:“来人!给本宫将她拿下!”
我大惊,焦急地问:“不知流心犯了何事?”
流心已被几个太监控制住,德妃走上前,手中忽地多出一个荷包,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流心做的,她当时熬了三天三夜缝制,为的就是送给她心仪之人方元。
德妃大怒:“宫中早有规定,禁止宫女和侍卫私通,违令者,杖毙。敢问皇后娘娘,现在该如何处置她?”
我怎么都没想到,德妃除了当众嘲讽我以外,竟给我这么大的下马威。
流心伺候我多年,在宫中无人陪我理我时,只有她从无怨言地跟着我,也是我唯一能说话解闷之人。她对我来说,不仅是侍女,更是知己姐妹。
她和方元定情在后宫本不是秘密,只因主子是我,我默默无闻,她自然也形同隐身,根本没人在意和刁难她。
但此刻,德妃竟将这事拿出来针对我,而我却不知应对。
我手心早已是汗,正盘算如何开口,德妃又说:“皇后娘娘身为母仪天下之典范,自然会以身作则,绝不姑息养奸,臣妾相信您定会做出抉择!”
我看着流心,她早吓得六神无主,只可怜巴巴地望着我。我心犹如在滴血,明明想的是不论如何都要救出她,可说出来的却是:“一切由德妃做主。”
是啊,我能拿什么救,我能如何救,我除了多出皇后的身份,其他仍旧什么都没有。
我还是那个我,还是那个胆小懦弱的定舒,连自己最关心的人都救不下,一无是处。
德妃满足地朝太监们点头,而后流心被拖出去,很快院子里就传来她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
我咬紧牙关,眼泪凝聚在眼眶中不断打转,打的是她,也是我。
大概我是历代最无能的皇后了,我突然很后悔,我宁愿不做皇后,宁愿回到那个没人理会的定婕妤。
兴许那样,我才能保护住身边最亲近的人。
4
妃嫔们离开时,流心被打得奄奄一息,好在德妃并没让太监直接打死,而是留了一条命。
我几乎是哭着冲到流心面前,望着她背上血肉模糊的伤,我心痛到快要死过去,大喊着让人快去叫御医。
御医来了,说是流心受伤太重,需要在床上躺几个月。
他开了药膏,我亲自给流心涂抹,涂在伤处时她痛得哭喊,我也忍不住眼泪直流:“都是我没护住你,都怪我没用,要是你主子不是我该多好。”
流心摇头,分明疼得脸都皱起来,却还安慰我:“怎么能怪娘娘呢,是她们太坏,她们根本不将娘娘放在眼里,她们迟早会有报应的。”
从屋中出来后,我便看着满院随风飘落的枯叶发呆,秋风瑟瑟,就如同我现在的心境,满心疮痍,悲痛不尽。
这个皇后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当了。
正想着,宫女突然朝我禀报,说是齐妃在外面候着,要亲自见我。
我一时奇怪,好端端地,齐妃为何要来见我,现如今妃嫔们都避我不及,她还来做什么。
宫女备好茶水,齐妃进来朝我行完礼,我这才仔细看她,今早只顾着注意德妃,未曾留意到她,现在一瞧,她面容憔悴,百般倦色,一看就知休息不足。
齐妃是皇上登基那年入宫的,也是后宫第一个为皇上诞下子嗣之人。尽管是小公主,皇上仍喜欢得不得了,她也算出尽风头。
只是这么多年过去,现在的后宫就如春天的繁花,一朵开败了,有的是将将绽放的娇艳欲滴。
皇上又哪里还会记得她呢。
齐妃看着我,看似关切地问:“皇后娘娘可还在为流心伤心?臣妾当时听着亦是心都揪起来了,免不了落泪。臣妾何尝不懂其中痛楚,只能眼睁睁看着,什么都做不了,让人绝望。”
这番话又让我想到流心,淡淡地道:“多谢齐妃关心,不过齐妃现在来是为何?”
她长叹口气,盯着我的眼说:“德妃此举明显是冲着皇后娘娘来的,今天只是流心,保不齐明日就会是您。难道皇后娘娘当真愿意一直被压着?”
我不知她是不是德妃派来的,只作糊涂:“流心做错理应受罚,德妃掌管后宫也应处置,德妃并未做错,说到底还是流心自己错了。”
她笑了,低声道:“皇后娘娘不用担忧,臣妾既不是德妃也不是丽妃的人,更和玉贵嫔没关系。臣妾过来就是想拥护您,以得到您的庇佑。”
她见我没说话,继续道:“不管德妃现在如何得意,她都只是妃,您才是我们大齐皇后。她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属于您的,您若拿回来,她就必须要还。”
我沉默不语,并不是她说的不对,只是凭我现在,我有什么资格叫她还。
再说了,那个高高在上的人都不松口,我又能如何拿回来。
我凄凉一笑:“齐妃今日的话本宫就当没听见,齐妃还是回去吧。”
然而她并没有要走的意思,反而勾唇一笑:“臣妾只想问娘娘一句,娘娘想不想拿回掌管后宫之权,只要您想,臣妾便有主意。”
我沉吟片刻,说不想是假的,我现在这境况和从前有何不同,可掌宫之权若都在我手上,又岂怕德妃。
我没回答,只问:“齐妃这么想帮本宫,对你有何好处呢?”
她脸色一下变得苍白,早无方才的斗志,喃喃开口:“臣妾之前不想参与任何纷争,只想好好抚养大小公主,但前几天胞弟不慎从马上摔断了腿,谈好的亲事也告了吹,臣妾母族的希望自此断落,是以今后一切都要靠臣妾了……”
“可这后宫早无臣妾的地位,只见新人笑,不闻旧人哭。德妃又一向打压臣妾,所以臣妾全部的希望都仰仗在您身上了,只要您答应今后掌权庇佑臣妾,臣妾便不顾一切助您得权!”
“难道您当真就愿意这么被德妃折辱?您好不容易坐上皇后之位,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她再抢走?您既然坐上了,就该拼命保住,该是您的谁也抢不走!”
“您到底还在迟疑什么?”
“本宫只是……不知你如何……”
“一切交给臣妾,您只管等着就行!”
看她如此成竹在胸,我终是点点头:“好,本宫答应你!”
5
半月后是二皇子清瑜的生辰,因是德妃的孩子,又是她亲自操办,生辰宴自然是办得热闹而喜庆。各宫妃嫔、各个府邸皆在邀请之列。
甚至为了让清瑜高兴,德妃还把和他同龄的朝臣家子嗣们接入宫,陪他一道过生辰,一道庆贺。
小孩子向来最喜欢糕点和皮影戏,是以德妃命今晚的御厨多做了好些糕点甜汤,又请了京都最好的戏班子入宫唱皮影戏。
宴席开始,我虽坐在皇上的身侧却形同多余,他的目光始终不曾瞧过我,更从未同我开过口。他一直望着右下侧的德妃和清瑜,显然他们才是今晚的主角。
皮影戏唱的是《大闹天宫》,孩子们看到高兴处跳起来拍手,清瑜则开心地跑到皇上面前,盯着他未动的糕点:“父皇,儿臣想吃一块蟹黄酥!”
皇上难得高兴,索性将他抱坐在腿上,然后喂给他吃,而他也十分享受,抓住皇上的手说:“父皇真好!”
这可让众人看羡了眼,德妃一时间风光无限,又哪里能是我来比较的。仿佛我的存在,更像是一个笑话。
看着面前一桌佳肴,吃在嘴里却如同嚼蜡,恨不得现在就拂手离去。
但我知道我不能,也做不到。
正当我数着树上有多少灯笼时,忽地就听有人在哭喊着叫御医,我立刻望过去,就见兵部尚书李可的小儿子李书福面色惨白,呼吸难以自持,口不能言,分明就是噎住了。
他手上还拿着半块点心,想必是吃得太急,又分外激动高兴,一不留神,只顾着说话便卡在喉咙口了。
李可夫妇几乎吓坏了,眼看御医再赶不过来,李书福随时有窒息的危险。
所有人都乱成一团,再看德妃的面色变得煞白,想必她也没想到宴会上会发生这种事,若李书福当真死在宴席上,不但她推卸不了责任,就连皇室的脸面都将折损。
我担忧地看着皇上,他剑眉紧皱,面上毫无表情,但眸中的寒意几乎能让人冷冻结冰。
李书福已经瘫倒在地,两眼翻白,就当他快无法呼吸时,我连忙冲过去,大声喊:“本宫有办法救他!”
我从背后抱住他,手中握拳,向上用力冲击他腹部,一次又一次,因力气过大,李夫人紧张地道:“皇后娘娘,您……您轻一点……”
德妃也来阻止我:“皇后娘娘究竟在干什么!御医很快就过来,您这样分明是在害他!来人!赶紧将皇后娘娘拉开!”